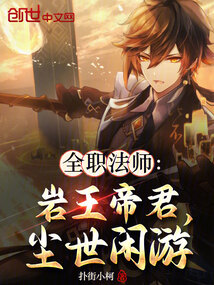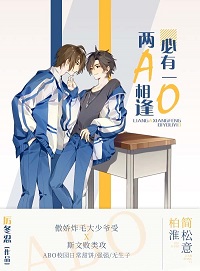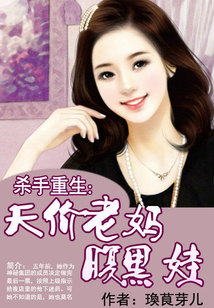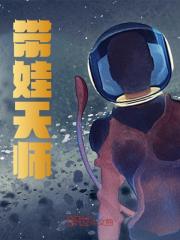第一章 梧桐镇的药香与哭声
大靖王朝,景泰七年的初夏,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沉郁些。
连绵的阴雨下了足有半月,梧桐镇西头的药铺里,沈青梧正跪在祖父的灵前,往香炉里添最后一撮艾草。烟丝袅袅升起,混着药柜里飘来的当归与陈皮味,成了这方小屋里唯一的暖意。
“祖父,今日该换新药了。”她轻声说着,指尖拂过灵前那本蓝布封皮的医书——《青囊秘要》。书角己经磨得发毛,内页夹着的药草标本却依旧平整,那是祖父行医五十年的心血,也是三天前咽气前,攥在手里不肯松开的东西。
三天前,镇上开始有人发高烧、上吐下泻,起初只是零星几户,祖父还说“不过是梅雨季节的时疫,几副藿香正气散便好”。可到了第二天,患者陡增,有人开始便血、抽搐,祖父背着药箱跑遍了半个镇子,回来时面色惨白,只来得及嘱咐她“守好药铺,莫信官府”,自己便倒了下去。
如今灵堂刚撤,药铺的门板还没来得及全卸下,就有人在门外跌跌撞撞地拍门,声音嘶哑得像被水泡过的破布:“沈姑娘!沈姑娘救命啊!我家娃儿快不行了!”
沈青梧起身,将《青囊秘要》小心地锁进祖父的樟木药箱,抓起墙角的出诊包。包上的靛蓝布条是去年她绣的,如今边角己被祖父磨得发亮,此刻随着她的脚步,在潮湿的空气里轻轻晃动。
开门的瞬间,一股混杂着汗臭与呕吐物的酸腐味扑面而来。门口跪着的是镇东头的王二柱,他怀里抱着个约莫五岁的孩子,孩子脸色青灰,嘴唇干裂,呼吸微弱得像风中残烛。
“沈姑娘,求您发发慈悲!”王二柱的膝盖在泥水里蹭着,“李大夫说治不了,县太爷又封了镇口,不让去城里……”
沈青梧没多问,伸手按住孩子的手腕。脉搏快而浮,像无根的浮萍,再看孩子的眼白,隐约有细密的红血丝——这症状,和祖父临终前一模一样。
“进屋说。”她侧身让王二柱进来,反手关上半扇门。药铺里光线昏暗,靠墙的药柜顶天立地,三百多个抽屉上贴着泛黄的标签,每一味药她都能闭着眼摸出来。她取了个粗瓷碗,从铜壶里倒出温水,又从出诊包里拿出一小包银针。
“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?”她一边消毒银针,一边问。
“昨天后半夜,”王二柱声音发颤,“起初只是喊冷,给他盖了三床被子还发抖,后来就烧得迷迷糊糊,开始吐……我听人说,前几日城西老张家的孙子,就是这么没的。”
沈青梧的手顿了顿。祖父生前最忌讳“没”字,总说“医者面前,只有能救和未救,没有‘没了’的说法”。她深吸一口气,将银针精准地刺入孩子的合谷、曲池两穴,手法稳得不像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。
“镇口被封了?”她问。
“今早刚封的!”王二柱急道,“县太爷说‘镇内无大事,勿要惊扰上峰’,还说谁敢往外传‘时疫’,就按‘妖言惑众’论处!李大夫就是因为多嘴,被衙役拖去打了二十板子,现在还躺在家呢!”
银针刺入的瞬间,孩子喉间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。沈青梧松了口气,又取过纸笔,写下药方:“葛根三钱,黄芩二钱,甘草一钱……去抓药,水煎服,每隔一个时辰喂一勺。”
王二柱接过药方,却没动,搓着手嗫嚅道:“沈姑娘,家里……家里实在没钱了……”
沈青梧看了眼药柜最底层的抽屉——那里放着祖父备下的应急药材。她没说话,转身拉开抽屉,抓出几味药包好,塞进王二柱怀里:“先拿去,钱的事以后再说。”
王二柱千恩万谢地走了,沈青梧刚把用过的银针收好,门外又传来敲门声,这次更急,还夹杂着女人的哭嚎。她拉开门,只见几个村民抬着门板,上面躺着个中年妇人,己经开始抽搐,嘴角溢出淡绿色的涎水。
“沈姑娘,她是第三个了……”为首的村民声音发颤,“都是这两天倒下的,我们不敢去报官,只能来求您了!”
沈青梧的心沉了下去。祖父说过,时疫最怕扎堆爆发,一旦出现抽搐、呕绿涎的症状,便是病入膏肓。她让村民把人抬到里屋的诊床上,刚要伸手诊脉,就听见街上传来马蹄声,还有衙役的呵斥:“县太爷有令!即日起,所有郎中不得擅自接诊,违令者与刁民同罪!”
药铺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村民们脸色煞白,有人己经悄悄往门口退。沈青梧抬头看向窗外,雨还在下,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,像一口倒扣的铁锅,要把整个梧桐镇焖熟在里面。
她握紧了手里的银针,针尖冰凉,却让她莫名镇定下来。祖父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:“青梧,医书可以残缺,但医者的心不能。”
“你们先把人抬到后院柴房,”她低声对村民说,“我去应付他们。”
转身时,她瞥见祖父的樟木药箱,箱子锁得很紧,蓝布封皮的《青囊秘要》就在里面。她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本医书,或许,还藏着能救梧桐镇的秘密。
门外的马蹄声越来越近,沈青梧深吸一口气,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门板。雨丝打在脸上,带着刺骨的寒意,而她身后的药铺里,三百多个药抽屉静静矗立,像沉默的战士,等待着一场硬仗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